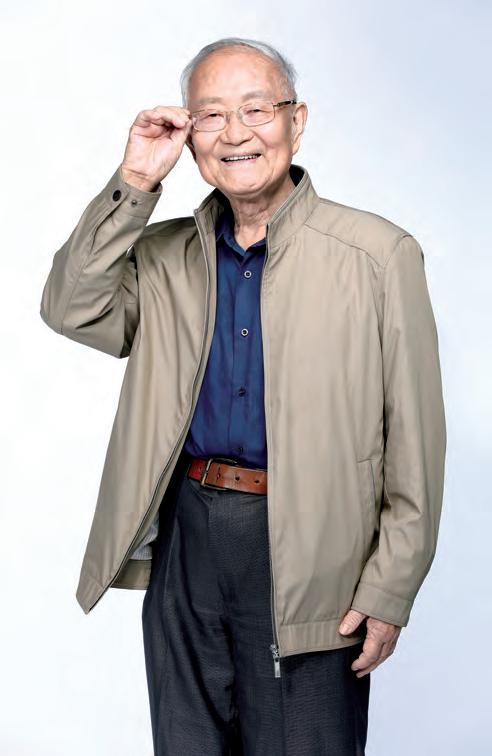
汪品先,1960年毕业于前苏联莫斯科大学地质系,我国著名海洋地质学家,同济大学海洋地质与地球物理系教授,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副主任,国际海洋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海洋研究科学委员会主席,中国海洋湖泊学会副理事长。
几十年来,汪品先学长努力推进中国的深海科学研究,先后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何梁何利基金奖等重大奖励多项。1999年春担任首席科学家,在南海主持了中国海区首次国际大洋深海科学钻探(ODP 184航次)。2006年起,成功推进我国海底观测系统的建立,由他指导的团队建立了中国首个海底观测试验站。2011年起,汪品先任国家“南海深部计划”指导专家组组长,使该计划成功发展成为我国最大的深海基础研究计划。
“我这辈子最想捕的‘大鱼’,终于捕到了!”汪品先所说的这条“大鱼”就是历时八年的“南海深部计划”。如今终于有了系统性成果。“我们终于可以说:南海不是小大西洋!”
南海位于三大板块交界处,地质活动剧烈,解开它形成与发展的奥秘,对了解我国的蓝色国土意义重大。近日,我国首个大型深海基础研究项目“南海深海过程演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画上圆满句号。
自2011年起,该项目由我国著名海洋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汪品先领衔,前后共有700多位科学家和研究生投入研究。他带领科学家们完成52个重点项目,经过3个半航次的国际大洋钻探、4个载人和遥控深潜航次的艰苦努力,通过对南海深部的系统性观测和分析,获得了新的认识,并对国际传统主流观点提出了挑战。
庆幸遇上最好的时代

作为1936年出生在老西门、成长在六合路的“老上海”,汪品先的童年记忆里有着苦难的深深烙印。在他只有八个月大时,父亲因逃难而亡故,母亲拖着他们兄弟三人清贫度日。汪品先上小学时,附近的慕尔堂是日本兵的营部,教堂门口有日本宪兵扛着枪把守,行人走过一定不能将两手插在裤兜里,不然就可能“挨枪子儿”。直到今天,他依然没有将手插裤兜的习惯。
“我是三兄弟中最小的一个。1949年,我和二哥都在格致中学上学,他高我两个年级,解放前就接触地下组织,时不时用报纸裹着进步书籍拿回家看,一解放就准备瞒着家里与同学一起‘南下’当兵,没有成行就得了伤寒去世。”汪品先说。
在格致中学的六年,对汪品先的影响很大。在格致中学建校145周年之际,汪品先应母校之邀,为母校迎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文集撰写序言道:“现在的同学,大概很难想象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母校师生那种热血沸腾的心情。在当时的革命巨浪里,同学们把进课堂学习和上前线参军,同样看成是投身宏伟事业的实际行动。”
直到中学毕业,汪品先和同学们总是抱着这种热情努力学习、参加社会工作。报效国家,就是当时学习的目标。上世纪50年代,地质找矿是国家的突出需求,加上格致中学解放后的第一任校长陈尔寿曾聘来一批造诣很深的地理学家给学生上课,燃起了青年人对地球科学的热情。因此,包括汪品先在内的不少学生,后来成了地质学家。
而当时的语文老师许志行,又为汪品先在独立思考上打下基础。还在解放之前,许志行就组织学生展开辩论,第一场辩论的题目就叫“要辩论还是不要辩论”,是当时教育界里的空谷足音。这种独立思考的习惯与能力,使汪品先一生受益。但凡与汪品先接触过的人,都会为他清晰的逻辑思维、充满热情与活力的言语而折服。
“可能没有哪一代人,会经历像我们这一代这么多的风雨飘摇与回转往复。如果不能独立思考,只是盲从,分不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真的很容易迷失自我,找不到自己的方向。”这是汪品先从自己在莫斯科大学留学的经历,以及后来的起起伏伏中,所体悟到的。正因为此,他才没有只埋首于学术,而是为破除种种时弊、为创新文化而奔走呐喊。
1953年,中学毕业的汪品先被选送到北京留苏预备部学习。与许多老解放区来的同学相比,从上海“十里洋场”来的汪品先,总带着一种“原罪感”,真诚地想改造自己,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批判个人主义。1959年,在莫斯科大学留学的最后一年,汪品先参加毕业实习,跟随老师一起翻过高加索山脉进行地质考察。但是当下到海边的时候雨后路滑,他们的汽车失控翻车。事后汪品先深感内疚,因为“当我醒来后,我的第一个念头是‘我还活着!’”他感觉自己的想法那么自私:为什么不是首先想到要救别人?这就是个人主义!他说,直到过了很多年,他才改变了想法,认为求生本能的反应并没有错。
“我们这代人的经历,现在的青年很难理解。”他说,“比如,思想上不自然的苛求是不真实的,因而也是误导的。”
在这个世界上,容易迷惑人的表象很多,要拥有真正让内心信服的理念,必须通过独立思考,看清未来的方向,义无反顾地坚持下去。“我是幸运的。”汪品先说,“尽管经历了几十年的风浪,无论从我工作的单位,学术界的同行,以至于自己的家庭,都能得到理解和支持,这就是幸福。”
自从在留苏预备部遇到了当时的班长孙湘君,汪品先就认准了她这个人生伴侣。哪怕曾经恋爱关系切断,哪怕为了海洋事业长期分居,这对科学伉俪始终相互扶持守候。在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的三楼,汪品先与夫人的办公室相邻,有一扇小门相通。平时,两口子一起去学校的食堂吃饭,食堂大叔总会将他们领到队伍的最前面,让这对八旬老人先打上饭菜——这可是校领导都没有的待遇。
深海大洋的无尽探索

1991年就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时称学部委员),可他却认为,直到1999年,自己的业务方向才算确立。“当登上国际大洋钻探船时,我感到自己终于找到了真正的人生方向。”
其实,汪品先在莫斯科大学学的并不是海洋,而是地质学里的古生物化石。从苏联留学归国后,汪品先来到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加入筹备中的“海洋地质系”。上世纪50年代末“全民找矿”的热潮兴起,上海也准备在海上找矿,但那时连陆上出差都困难,遑论海洋!
多年以后,国家在上海设立“627工程”准备东海、黄海的石油勘探,方才出现了机会。在1969年“文革”下乡期间,汪品先与几位同事起草的建立海洋地质系的建议很快被采纳。1970年,华东师范大学开始招收海洋地质系本科生。1972年,当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地质局一份通知,将该系转到同济大学,与同济的水文地质专业合并到“地下工程系”,于1975年正式挂牌成立海洋地质系。
在那个国民经济百废待兴的年代,学校连一条小舢板都没有!怎么去海里找石油?汪品先回忆,靠一些出海的船只带回黄海海底的泥巴,他带着学生用吃饭的大搪瓷碗将泥巴泡开,然后在厕所的自来水龙头下淘洗,再在一台勉强可用的显微镜下观察——就这样开始了向海洋科学“进军”的第一步。
“我最感到幸运的是,‘文革’结束后,我成为同济大学最早出国的老师。”汪品先说,1978年9月跟随当时石油部科技代表团出访美国和法国,使他顿然开了眼界,“中国要跻身世界海洋科研”的愿望,在心头勃然而生,历久弥坚。
就在那次出访时,有一位法国专家在饭桌上向汪品先介绍乘坐载人深潜器潜入地中海海底的经历:“漂亮极了,到处都是海百合,安静得没有一点声音。”套用一句90后的流行说法,汪品先成功被这位教授的话“种草”了。直到40年后的2018年,汪品先才如愿以偿,以82岁高龄首次搭载“深海勇士”号4500米载人深潜器,在南海完成3次1400米水深以下的下潜,实现他追寻了大半个人生的目标。
1977年,他应邀去海南岛参加南海第一口探井“莺1井”的地层分析,从此和南海石油勘探长期合作;1980和1984年,在同济先后举办了碳酸盐和古海洋学的国际讲习班;1981年,汪品先获得洪堡奖学金去德国基尔大学深造,那里正是德国的海洋中心;1988年,“第一届亚洲海洋地质大会”在同济召开。种种进展,都为同济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前提。
此后几年里,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当选学部委员、建立海洋地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汪品先在忙碌中开始反思:为何我国的海洋地质科研看起来干得轰轰烈烈,却难以获得国际学术界关注?在分析了国际海洋科学前沿动态后,汪品先决定将科研方向从近海转向深海。
机遇来了!始于上世纪60年代的“深海钻探计划”于1985年结束了,而新的“大洋钻探计划”开始了。中国科学家一定要介入!尽管那是一个“富人俱乐部”,每年要支付数以百万计的美元才能成为会员国——这在30年前的中国无异于天文数字。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1997年国务院批准参加国际大洋钻探;同年,由汪品先执笔的南海钻探建议书,在国际评比中以第一名的成绩脱颖而出。1999年2月,汪品先作为南海航次的两位首席科学家之一,登上钻探船。
“当钻探船从澳大利亚西部启航驶向南海时,我在甲板上感慨万千,感到自己终于成为名副其实的海洋地质学家。”汪品先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从长江口起步,到实现大洋钻探的深海探索,我个人经历了30多年……两个月的南海大洋钻探,取上了5000多米质量空前的深海岩芯,提供了3000多万年来环境变迁的连续记录……”
就在大洋钻探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我国的海洋事业也在蓬勃发展:海洋科考船陆续兴建、7000米载人深潜器“蛟龙号”启动研制、海上钻井平台不断发展……2011年,在大量前期铺垫之下,国家“南海深部计划”终于启动,汪品先任指导专家组组长。此时,翦知湣、周怀阳等一批中青年科学家也已挑起了科考的大梁。
“我们终于用自己获得的海洋地质样品数据,形成了自己的新观点,挑战传统的认识。”汪品先说,过去很多理论往往以欧洲、北半球为中心,但从很多新的证据来看,可能很多理论并不一定站得住脚,“是时候提出中国科学家的理论和观点了”。
开“抖音”、玩儿“B站”,这位院士有点“潮”

80多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汪品先最近有点“潮”。他不仅开通了“抖音”玩起小视频,还干脆把课堂搬到二次元社区哔哩哔哩网站玩起了直播。
汪品先在同济大学开设的《科学与文化》课程第二讲“科学与视野”直播上线。不到2个小时,观众累计达到12万人次。
《科学与文化》的课程内容与他的专业有关,但远不止海洋地质。一共8讲内容中,包括科学的产生、科学与视野、人类与海洋、科学与好奇、创新与教育、东西方文化、科学通用语、地球的未来等,“文化”作为主线贯穿其中。
“我就是想要‘鼓吹’文化。”汪品先认为,科学创新要有文化元素。文化,要注入科学进展的新鲜血液;科学,要点亮文化积累的智慧之光。两者是相通的,都是创造性思维的产物。
很多科学家,乃至院士,很少愿意面对公众,更不愿意面对媒体。但汪品先是个例外,他愿意发表自己的观点,愿意引起争论与共鸣。其实,他并不想成为“网红”,只是希望通过自己一记记的“重锤”,为中国科研的发展,破除一些思想观念上的禁锢、纠正一些谬误,让开拓创新之路上的后来者,可以少一些障碍。
汪品先两次与文汇报合作,共同发起“创新障碍在哪里”“如何重建创新文化的自信心”的大讨论,在知识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投身科学,第一层次是好奇心驱动,第二层次是成就感驱动,第三层次才是名利心驱动。汪品先一直认为,海洋也代表着一种文化属性。他希望,中国文化可以吸纳更多有利创新的元素,“我总感觉希望在未来”。
(根据文汇报、中国科学报整理)